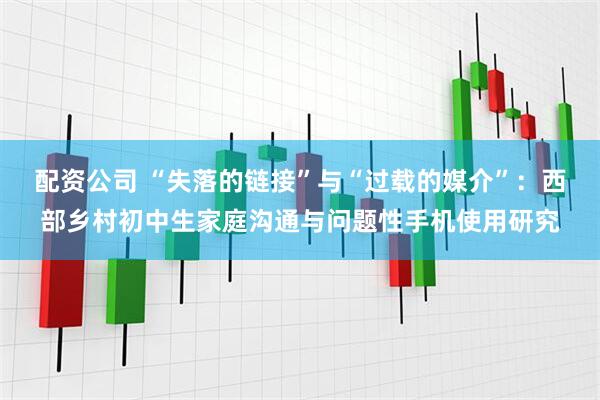
 配资公司
配资公司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因青春期特质与地域限制,易陷入问题性手机使用困境。家庭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社会化场域,揭示其内部沟通模式及其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机制,对理解与改善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601名西部乡村初中生的心理与行为数据发现:(1)在我国西部乡村地区约858.73万名初中生中,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整体发生率达31.6%至39.2%,高于国内外同龄群体,且男生尤为严重;(2)受西部儒学传统与现代教育思潮双重影响,西部乡村家庭沟通呈现“权威-服从型”“引导-服从型”“尊重-对话型”三种模式;(3)家庭沟通模式显著影响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其中“引导-服从型”更容易催生其孤独情绪,进而正向预测问题性手机使用,这种内生于家庭的孤独在高水平学校联结的调节下,其中介效应进一步被强化。由此,解决“媒介过载”的关键在于弥补家庭内部的“链接失落”。
作者简介
张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吕卓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肖林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项目(项目编号:2722023BY011)的阶段性成果。
一
研究缘起
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现象近年来日益严重。据《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有两成青少年承认自己对手机存在依赖心理。
在我国乡村地区,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发生率逐年增加(Wang et al.,2023)。已有研究表明,乡村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率(29.3%—29.4%)显著高于城市青少年(22.5%—23.4%)(Cheng et al.,2024;Wu et al.,2023)。此外,西部地区中学生的手机依赖率(26.4%)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9.0%—22.8%)(Wu et al.,2023)。同时,初中生因青春期生理与心理特征,容易呈现出更强的手机使用依赖性与脆弱性(Shi,Wang & Zou,2017)。
在此背景下,西部乡村地区初中生不仅面临青春期固有的脆弱性,还受到乡村与区域发展的双重影响,这使得他们在应对手机成瘾问题时可能更加脆弱。据估算,我国西部乡村约有858.73万初中在校生,但学界对该群体问题性手机使用的研究仍显不足。基于此,探究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的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成为本文第一个研究目标。
在技术依赖和问题性使用背后,家庭环境扮演关键角色。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照料者,父母通过物质联系与情感支持,塑造了其最初级的自我意识(Bretherton,1990)。同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家庭”被衍生出不同意义,学界逐渐将“家庭传播”作为自变量,用以解释微观层面个体的社会互动以及宏观层面社会结构的变迁(朱秀凌,2018)。其中,“家庭传播”如何影响未成年人心理与行为,已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相比于西方家庭传播研究的日臻成熟,中国相关研究尚处起步阶段,目前仍集中于引介西方理论与方法,大多数研究将中国案例嫁接到家庭沟通模式理论(高芳芳,张佳楠,2023)、父母介入理论(朱秀凌,2021)等国外理论框架中,尚未形成与本土文化相适应的研究范式。
根据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中国作为高语境文化国家,人际传播的关键信息往往隐含在语气、语调、动作、表情等非语言环境中,而非语言文本本身。与美国等西方低语境文化国家直接、明确的符号编码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家庭更倾向于使用含蓄、间接的信息传递方式。此外,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长辈权威与家庭等级制度,使家庭沟通呈现出有序、和谐等特征,并蕴含着面子文化(翟学伟,周丹丹,张涛,2023)。乡村以“父子人伦”为主轴、“孝道”为核心,与“家庭”共同构成了中国伦理精神的两大源泉。因此,本文以此为基础,将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传播模式作为第二个研究目标。
社会建构主义指出,乡村社会结构通过日常实践不断塑造着乡村青少年(郑春风,2023)。除家庭外,学校在满足其社会需求、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借助手机和互联网,乡村青少年可以维持与父母、同学间的“强关系”,并从中获得情感支持(陈阳,郭玮琪,2022)。基于此,本研究第三个目标是从传播学与心理学交叉视角出发,勾连出西部乡村家庭沟通模式、孤独、学校联结与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潜在关系,深入分析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心理行为机制,从而为其合理使用媒介提供指导,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与媒介技术使用的“乡村振兴”。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一种心理依赖现象”:问题性手机使用的界定
“依赖”一词源于医学,多指对酒精、药物等物质的依赖,后逐渐扩展至网络、手机等技术应用领域,研究亦逐步聚焦于由此类技术引发的“成瘾”行为。在“技术成瘾”的基础上,Bianchi和Philips(2005)首先提出了“问题性手机使用”(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的概念,认为对手机不恰当使用以及过度使用是一种问题行为。学界也存在“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智能手机成瘾”(smartphone addiction)等类似表述,大多将其归为由技术导致的行为成瘾范畴,即因过度沉迷手机而导致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受损现象,通常伴随失控、耐受性与戒断反应三个关键心理特征(Billieux,2012)。外在表现包括强迫性无意识检查手机、频繁“幻听”、忽视其他活动、在开车等不适当环境中使用手机等(Busch & McCarthy,2021;Kabadayi,2024)。基于此,本文认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受控制地渴望使用或实际存在过度使用手机并产生了相关不良行为时,即可认为出现了问题性手机使用,它是一种多维度的心理依赖现象,不仅仅是使用时间与频率过度的问题。
尽管大量研究探讨了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现状及机制,但针对西部乡村等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为匮乏。一方面,与城镇父母相比,乡村地区父母在“家庭共养”“家校共育”方面相对薄弱。手机常成为父母在农忙时期或外出务工期间照看子女的“电子保姆”,导致青少年更容易被忽视并产生孤独等负面情绪(Wang et al.,2023)。同时,由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生活资源有限,青少年难以从学校和家庭中获取足够的心理和物质支持,更容易转向虚拟空间(Wang & Li,2019)。
另一方面,在不同学龄段中,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风险最高(Shi,Wang & Zou,2017)。这一年龄段的青少年对于网络中的即时奖励等兴奋的内抑制发育尚未成熟(林崇德,李庆安,2005),相比于高中生,他们的自控能力更弱,而网络又满足了其在现实中受限的独立需求和自我表达渴望,使之表现出更强的手机使用依赖性和脆弱性。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于西部乡村初中生的问题性手机使用。
(二)“基于依恋的依赖”:家庭沟通与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关系
根据依恋理论,从婴幼儿时期开始,父母就通过亲子互动塑造其对人际关系的感知和期望,进而影响其行为方式、社会认知的发展(Bretherton,1990)。不安全依恋关系不仅与药物滥用、酗酒等物质成瘾行为相关,还导致游戏沉迷、问题性网络使用等非物质成瘾行为(Estevez,Jauregui & Lopez-Gonzalez,2019)。
亲子间言语及非言语的沟通过程,不仅是依恋关系产生与维持的基础(Bretherton,1990),亦对儿童与青少年时期的依恋安全建构起到关键作用。不良的家庭沟通模式会对青少年互联网成瘾等行为产生深远影响(Liu et al.,2019)。基于此,本研究从家庭沟通入手,旨在探究其对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机制。
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提出了基于对话导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与服从导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的二维家庭沟通模式,并以中位数为界划分出多元型(pluralistic)、保护型(protective)、一致型(consensual)和放任型(laissezfaire)四类家庭沟通模式。多元型家庭(低服从、高对话)鼓励自由表达与平等交流;保护型家庭(高服从、低对话)则强调权威与服从,限制开放对话;一致型家庭(高服从、高对话)在鼓励表达的同时要求服从;放任型家庭(低服从、低对话)则表现为亲子间互动匮乏(田娇,黄合水,2023)。
尽管国内部分学者采用四分类法进行研究,但其研究假设与结论讨论仍聚焦于对话、服从两个核心维度展开(朱秀凌,2021)。其中,对话导向反映亲子沟通中观点分享程度,高对话导向的家庭鼓励子女表达思想;服从导向则强调观点、态度一致,高服从导向的家庭沟通更倾向于要求子女顺从父母,限制其表达异质性观点的机会(高芳芳,张佳楠,2023)。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高对话导向的家庭沟通有助于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心理行为发展,高服从导向沟通方式则可能增加包括互联网成瘾在内的多种负面心理行为风险(Liu et al.,2019)。
作为最基本的家庭沟通维度,对话与服从导向二维家庭沟通模式在东西方文化中均具有广泛适用性,可能也是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中国家庭沟通方式深受千年农耕文明的影响,强调家族价值、尊老爱幼和集体和谐,正因如此,西部乡村家庭沟通更强调长幼有序。另一方面,工业化与城乡结构转型对传统乡村社会形成挑战,导致“乡土”向“离土”转变(朱茂静,2023),平等对话观念逐渐渗透。在传统与现代沟通方式交融碰撞的背景下,家庭内部逐渐形成了复杂的沟通动态。例如,乡村父母通过外出务工、互联网参与等方式广泛接触到西方教育理念,从而鼓励子女自由表达,这与传统的含蓄表达、自我牺牲观念形成冲突,使得中国家庭沟通在对话、服从导向的基础上呈现出更为多维的沟通模式。
虽然四分类法(多元型、保护型、一致型、放任型)在对话、服从的维度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但其以中位数划分的方式较为简化,导致分类结果具有一定任意性,可能掩盖了实际差异(Ritchie & Fitzpatrick,1990)。因此,本文使用聚类分析代替中位数划分,基于样本相似性自发形成群体(Kayri,2007),避免人为设置阈值的局限,能更灵活地捕捉家庭沟通中的细微差别,以更准确地揭示家庭沟通模式的真实结构。
综上,本文在保留二维家庭沟通模式作为理论基础的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部乡村社会特点,探索西部乡村家庭沟通模式及其对初中生手机使用行为的影响,以挖掘中西方理论对话的空间,避免对西方理论的直接套用。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和假设:
RQ:新时代的中国西部乡村呈现出哪些家庭沟通模式,又有哪些独特之处?
H1:不同的家庭沟通模式会对西部乡村初中生的问题性手机使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作为情感的补偿”:孤独的中介作用
家庭沟通对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路径较为复杂,研究表明,焦虑、抑郁、害羞、孤独和自卑等个体心理因素在家庭互动与青少年互联网使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Shi,Wang & Zou,2017)。在青春期这一重要的过渡阶段,青少年的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孤独”成为其主要情绪体验之一。对于“留守在家”或“陪伴缺位”的乡村青少年而言,情感缺失导致的孤独感更为显著(杨钋,颜芷邑,2022)。
根据社交需要理论与认知加工理论,当家庭沟通无法满足初中生的情感需求与认知期待时,孤独就会产生(谢华,苟萍,2007)。大量研究证实,家庭环境、亲子关系对孤独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Shi,Wang & Zou,2017)。此外,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指出,个体通过使用互联网或手机缓解孤独等负面情绪(Kardefelt-Winther,2014)。由于缺乏现实的密切社交网络,孤独感越强的个体越容易被线上虚拟社交所吸引并形成依赖。现有研究结果大多支持孤独与手机成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Shi,Wang & Zou,2017;Wang et al.,2023)。
可见家庭沟通在塑造初中生情绪与心理状态方面起关键作用,孤独作为其重要结果,往往会推动初中生产生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孤独在家庭沟通模式与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不同的家庭沟通模式会对西部乡村初中生的孤独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孤独感越强的个体,越容易产生问题性手机使用。
(四)“来自学校的缓冲”:学校联结的调节作用
随着我国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及“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进,大量西部乡村中小学生不得不前往距家较远但教育资源集中的地区上学,寄宿制学校逐渐成为乡村地区主要办学模式(杨钋,颜芷邑,2022)。除寒暑假外,大多数初中生每周五天在校寄宿,仅周末回家,学校成为除家庭以外,满足其互动需求与情感联结的另一重要环境。因此,通过同伴和教师支持以及学校归属感来衡量的学校联结,作为初中生积极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不仅是学生健康行为、幸福感、学业成就等的直接保护性因子,也成为考察个体因素与发展结果关系间的重要变量(叶苑秀,喻承甫,张卫,2017)。
根据依恋理论,学校联结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和资源,能够抵消问题性手机使用等负面行为(喻承甫等,2011)。同时,“缓冲模式”指出,一种良好的关系可以缓冲其他一种不良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田菲菲,田录梅,2014)。积极的学校环境为学生提供的替代性支持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中父母关爱的缺失对初中生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已有研究证实,学校联结在心理情绪对负面行为的预测中具有调节作用(喻承甫等,2011)。对于学校联结较强的西部乡村初中生而言,他们即使感到孤独,也可能有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来应对,从而减少因孤独而导致的问题性手机使用。反之,在学校联结较弱的情况下,初中生因缺乏现实支持与理解,可能更容易受到孤独的影响,进而出现问题性手机使用现象,因此,学校联结可能在孤独与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发挥贡献型调节作用(Holbert & Park,2020)。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学校联结是孤独与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预测关系的贡献型调节变量。具体表现为,学校联结越强的西部乡村初中生,孤独对其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正向预测作用越弱。
综上,本文构建出如图1所示的研究模型,并提出三个具体的研究目标:(1)探究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的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2)在二维沟通模式的基础上,实现中国西部乡村家庭沟通模式的在地化;(3)结合孤独的中介作用与学校联结的调节作用,探索其对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潜在影响。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获取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地区分类,我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个省份。从中随机抽选西南地区的四川省、西北地区的甘肃省代表我国西部地区。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与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式,以学校与班级为主要抽样单元,于2023年6月在甘肃省和四川省便捷选择5所乡村初级中学进行问卷调查。由于九年级学生临近中考,研究仅从七年级、八年级中系统抽取22个班级。班级内所有同意参与调研的学生共计615名,最终回收有效问卷601份,有效率为97.72%。包括298位男生(49.6%)与303位女生(50.4%);年龄范围为12至17岁,平均年龄13.98岁(SD = 0.82),其中留守儿童147人(24.5%),非留守儿童454人(75.5%)。
调研以匿名进行、以班级为单位统一施测,每班配备1名经专业培训的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作为主试,被试完成问卷的平均时间约为20分钟,问卷完成后由主试统一回收。本研究获得了伦理审批,并取得被试学校、青少年及其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确保青少年隐私得到保护。
(二)测量工具
1. 家庭沟通模式
本研究采用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开发的修订版家庭沟通模式(RFCP)量表。该量表共26个题项,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评分(“非常不同意”= 1,“非常同意”= 5)。其中,对话导向包含15个项目(例如“父母鼓励我表达与他们不同的想法和观点”,Cronbach ’s α = 0.92);服从导向包含11个项目(例如“父母经常说‘孩子不应该和成年人争论’”,Cronbach’s α = 0.82)。
2. 孤独
采用Russell(1996)修订的修订版第三版UCLA孤独量表,该量表采用四级评分(“从不”= 1,“总是”= 4),共20个题项,如“你常感到没人可以信赖吗”等(Cronbach’s α = 0.90)。
3. 学校联结
中文版量表。该量表由10个题项组成,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评分(“非常不同意”= 1,“非常同意”= 5),涵盖了三个维度:教师支持(如“我觉得老师关心我”)、同伴支持(如“在发生困难时我可以依靠我的同学们”)和学校归属感(如“我觉得自己是学校的一份子”),Cronbach’s α = 0.87。
4. 问题性手机使用
采用由Foerster等人(2015)编制的问题性手机使用量表(MPPUS-10),该量表是MPPUS-27的简洁版(Bianchi & Philips,2005),由10个项目组成,与后者的内部一致性已得到广泛验证(r = 0.95),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评分(“完全不同意”= 1,“完全同意”= 5)。题项包括“我发现关掉我的手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等,项目得分加总反映问题性手机使用水平。目前,MPPUS-10已经有多种语言版本,且在本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α = 0.91)。
特别指出,MPPUS-27总分为270分(27个项目),精神病学访谈黄金标准验证得出160分为问题性手机使用的高度敏感点,得分占比为59.26%(Kalhori et al.,2015)。根据普遍采用的MPPUS-27转化为MPPUS-10的阈值设定方法(Nahas et al.,2018),本文将临界值外推到27分(总分为45分,得分占比为60%,大于59.26%),即得分大于等于27分者将被认为存在问题性手机使用,以严格遵循阈值设定。
5. 控制变量
此外,为更好地理解所研究的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将性别、年龄以及是否为留守儿童设置为控制变量。
(三)分析方法
为回答研究问题,首先运用二阶聚类分析识别家庭沟通模式的潜在类别。随后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与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估量表的共同方法偏差与结构效度。最后,采用调节中介模型检验孤独的中介效应及学校联结的调节作用,并控制性别、年龄和留守状态。
四
研究结果
(一)1/3西部乡村初中生存在问题性手机使用
对601名西部乡村初中生的调查显示(表1),问题性手机使用均分为23.18(SD = 9.05),孤独均分为2.32(SD = 0.78),学校联结均分为3.76(SD = 0.93)。其中,212名学生(35.3%)问题性手机使用得分达到或超过27分的临界值。具体来说(表2),131名男生(44.0%)报告存在问题性手机使用,显著高于81名女生(26.7%),χ2 (1,N = 601)= 18.78,p < 0.001。留守儿童中57人(38.8%)报告问题性手机使用,略高于非留守儿童的155人(34.1%),不存在显著差异,χ2(1,N = 601)= 0.85,p = 0.356。
基于样本数据对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发生率进行推断性统计,结果显示其估计值为35.3%,95% CI [0.316,0.392],这表明至少有271.4万名西部乡村初中生可能存在问题性手机使用。

(二)信效度及模型拟合良好
本研究采取被试自我报告方式收集数据,故通过Harman单因素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CMB)。结果显示:KMO = 0.91,Bartlett值为11835.87,p<0.001,提取出6个特征值大于1.0的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63.45%(高于60%),且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4.04%(低于40%),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进一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评估测量模型的拟合度,结果显示:x2/df = 2.538;RMSEA = 0.051;NFI = 0.878;IFI = 0.922;CFI = 0.922,模型整体拟合良好。因此,研究模型结构效度和信度均达到满意水平。
(三)基于聚类结果的中国西部乡村家庭三大沟通模式及特点
为探讨我国西部乡村家庭沟通模式的差异性,本研究使用IBM SPSS 27.0对样本的家庭沟通模式进行二阶聚类(two-step cluster analyze)。二阶聚类作为一种探索性聚类方法,可以在未知具体类别数量的情况下,自动检测出样本间的潜在关系与类别并确定最佳类别数量(Kayri,2007)。SPSS自动生成三种聚类结果(表3),显示我国西部乡村家庭主要呈现如下沟通模式:
聚类1:“尊重-对话型”沟通(N = 179,29.8%)。该聚类代表具有高对话沟通(M = 4.23)和低服从沟通(M = 1.98)特征的家庭。这类家庭尊重并倾听初中生的意见,注重频繁、有效的对话式交流,鼓励自由表达并提供实际支持。
聚类2:“引导-服从型”沟通(N = 217,36.1%)。该聚类家庭表现为高对话沟通(M = 4.21)和高服从沟通(M = 3.96),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指中国传统乡村人际网络如同水波纹,呈现出远近亲疏的差异。在此背景下,乡村父母常将子女视为“自我”的延伸,对话沟通虽表面开明,但实际目的是引导子女服从。此外,这种模式也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五伦”,强调人际互动需明确身份差异与等级规范(翟学伟,2016)。
聚类3:“权威-服从型”沟通(N = 205,34.1%)。该聚类家庭表现为弱对话沟通(M = 2.62)和较强的服从沟通(M = 3.34),与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一致。古代社会因生产力不发达,为增强家族凝聚力,形成了“父权权威式”的家庭伦理和严格、专制的家庭教育氛围。在此沟通模式下,家庭教育以压力、严格管控为特征,父母要求初中生在思想与行为上与自己保持一致,导致初中生的言论与行动自由受限、需“被允许”。

(四)孤独的中介效应显著,学校联结的调节作用成立
由于本研究的自变量为三水平有序类别变量,因此需选择某一水平作为参考。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兼具最高对话导向与最低服从导向的“尊重-对话型”沟通(聚类1)为参考水平,采Helmert编码法生成D1、D2两个虚拟变量(方杰,温忠麟,何子杰,2023)。除自变量以外,中介变量(孤独)、因变量(问题性手机使用)以及调节变量(学校联结)均为连续变量。
基于此,采用SPSS的macro PROCESS v3.5运行model 14,检验调节中介效应,并控制性别、年龄和留守状态(表4)。具体分析如下:在模型1中,相较于“尊重-对话型”家庭沟通模式,“引导-服从型”沟通和“权威-服从型”沟通均显著影响孤独(D1:β = 0.413,p < 0.001;D2:β = 0.304,p < 0.001)。在模型2中,“引导-服从型”沟通显著正向影响问题性手机使用(β = 1.865,p < 0.05),而“权威-服从型”沟通对其并无显著影响(β = -0.763,p > 0.05)。这表明,与“尊重-对话型”和“权威-服从型”相比,“引导-服从型”家庭沟通模式更能正向、直接地预测问题性手机使用,因此H1成立。

进一步检验调节中介效应,如表5所示:相较于“尊重-对话型”,“引导-服从型”沟通模式的调节中介效应显著(Effect = 0.526,SE = 0.252),95% CI [0.087,1.092],表明学校联结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当学校联结低于一个标准差时,相对中介效应为0.838(SE = 0.355),95% CI [0.152,1.539],相对中介效应显著。当学校联结高于一个标准差时,相对中介效应为1.814(SE = 0.420),95% CI [1.057,2.693],相对中介效应同样显著。由此得出结论:高水平学校联结下,相较于“尊重-对话型”家庭沟通模式,孤独在“引导-服从型”沟通对问题性手机使用影响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更强。
相较于“尊重-对话型”家庭沟通模式,“权威-服从型”沟通模式的调节中介效应同样显著(Effect = 0.387,SE = 0.201),95% CI [0.061,0.833]。当学校联结低于一个标准差时,相对中介效应为0.617(SE = 0.288),95% CI [0.106,1.226],相对中介效应显著。当学校联结高于一个标准差时,相对中介效应为1.334(SE = 0.390),95% CI [0.631,2.146],相对中介效应同样显著。由此得出结论:高水平学校联结下,相较于“尊重-对话型”家庭沟通模式,孤独在“权威-服从型”沟通对问题性手机使用影响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更强。

总而言之,在家庭沟通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机制中,孤独的中介效应显著且因学校联结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H2成立。学校联结是孤独与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贡献型调节变量,但其调节作用与H3假设方向相反,具体表现为学校联结越强,孤独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正向预测作用越强,H3部分成立。
五
讨论与结论
(一)“整体不容乐观且男生尤为严重”: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现实
研究发现,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发生率应在31.6%至39.2%,高于全国、西部地区及乡村地区水平,也超过韩国等国家的中学生数据(Cheng et al,2024;Wu et al.,2023)。
此外,男生问题性手机使用发生率(44.0%)显著高于女生(26.7%),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Shi,Wang & Zou,2017)。男生更容易沉迷于手机游戏和娱乐应用,可能是因其更倾向于通过手机来寻求刺激性和竞争性(Li et al.,2023)。学习倦怠社会导向理论也指出,男女两性会由于性别分工以及社会角色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手机依赖特征(Wang et al.,2023)。因此,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尤其是男生的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亟需重视。
(二)“潜意识地要服从与被服从”:独特的西部乡村家庭沟通模式
我国亲子关系深受儒家孝道原则影响,强调尊敬、服从、照顾甚至“牺牲”。与西方四分类家庭沟通模式不同,本研究发现我国西部乡村家庭沟通模式可以分为“权威-服从型”“引导-服从型”“尊重-对话型”三种,其中“对话导向”依次递增、“服从导向”依次递减。这不仅反映了西部儒学对乡土社会的深远影响,也揭示了“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父母平衡传统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冲突与困惑。
“权威-服从型”家庭强调子女对父母权威的遵守,父母在沟通中占主导地位,限制子女的自我表达。这种沟通模式体现了西部乡村儒学与父权制结构。与东部工业型乡村和中部空心化乡村不同,西部乡村因地理封闭、远离市场中心,传统农业生产得以保留。尽管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务工动力较弱,常在外出与返乡间徘徊。这种相对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外部观念的渗透,使传统生活观念和仪式性人情互动得以延续,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风俗进一步滋养了村庄的公共生活与传统儒学思想。同时,在这里,儒学与藏族、羌族、回族等民族的传统思想交融,强化了家庭中的父权制结构(舒大刚,段博雅,2021),使西部乡村家庭注重“父父子子”的传统模式,父亲延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儒家理念,形成了权威式的传统中式教育。
与“权威-服从型”相反,“尊重-对话型”家庭沟通模式显现出在现代工业文明影响下,西部乡村家庭形成的以互相尊重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道德。尽管占比最少,也展现了部分西部乡村家庭在现代文明影响下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颇具“蒙氏教育”特点。家庭成员优先考虑充分沟通与自我表达,父母更为重视与子女的相互理解与积极倾听。
相较之下,“引导-服从型”家庭沟通在调查中占比最高,折射出中西方家庭沟通差异及西部乡村家庭沟通的独特图景。表面上看,这种模式似乎表现出开放、平等的家庭沟通,但实际上对初中生的服从度有较高要求,使“对话”与“服从”高度共存。这种独特沟通模式的产生可能与西部乡村“半工半耕”的弹性劳动力配置方式相关。虽然西部乡村中青年外出务工比例(约30%)低于中部(杜鹏,2024),但两地仍形成类似的劳动力配置,即父母双方或一方进城务工获取货币收入,祖辈或另一方务农以获取农业收入(朱茂静,2023)。与上一代相比,新生代进城务工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试图突破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交圈,开始以城市生活为导向,倾向于选择服务业或普通岗位。在以服务业为主的“半工”过程中,他们受到城市消费、教育等方面冲击,产生了更强的阶层意识,渴望“脱离农门”并落户城市,同时开始重视子女教育,形成较高的教育期待(黄丽芬,2021)。基于个体生活轨迹,他们建构了以熟人为主的“圈层结构”,并通过与城市家长接触或网络浏览,逐渐接受现代教育理念,尝试以更开放的方式与子女沟通,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他们在和子女互动中呈现出形式上的平等,如使用平等称谓、积极倾听等。然而,“孝道”与“家族”观念在中国亲子关系中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尽管父母会努力营造平等自由的沟通环境,子女的意见似乎得到重视,但实际上父母仍认为自己拥有绝对正确性,引导子女遵循其期望,使子女在潜移默化中服从。最终,子女期待被搁置,形成了“浅层次对话、深层次服从”的尊重与监督共存的复杂沟通模式以及“潜意识地要服从与被服从”的亲子关系。
(三)“表象之下的逃避”:家庭沟通模式对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预测
与假设一致,家庭沟通模式显著作用于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与先前研究相符,不同家庭沟通模式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各不相同(Liu et al.,2019)。与“尊重-对话型”的家庭沟通模式相比,“引导-服从型”沟通模式可以显著预测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而“权威-服从型”沟通模式则不显著。
这一结果的潜在解释路径是,“尊重-对话型”的家庭建立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初中生无需过于向手机诉诸话语表达与情感宣泄,而“权威-服从型”的家庭往往对初中生手机使用等行为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和约束。
“引导-服从型”沟通模式最为“别扭”,体现出我国很多家庭在亲子关系中的“拧巴感”——或是有爱却不言爱,或是“爱之深、责之切”、将亲子矛盾冲突进行简单归因与合理化,抑或是沟通尽头那句“都是为了你好”及其所代表的“强制爱”。这种看似尊重子女话语权的表象之下,实则暗含我国西部乡村家庭,甚至是中国家庭沟通中的等级差异。在亲子实践中,父母可能并没有真正优先考虑或关注子女所表达的意见和情感。
这也与中国“高语境文化”有关,语言本身只是信息的载体,态度、语气及眼神等非语言行为才是信息表达的关键。父母语言上的平等不代表子女感受不到压力。 “引导-服从型”模式虽然表面温和,却可能加重青少年的自我归因倾向,导致其将沟通障碍内化为自身问题,并产生自我怀疑,导致他们通过手机寻求情感表达与他人认同,以弥补在家庭沟通中感受到的挫败感。这也与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相一致,当人们遇到消极的生活现状时,可能会通过网络或手机来缓解负面情绪,其实质是对现实的逃避(Kardefelt-Winther,2014)。相比之下,“权威-服从型”模式的青少年则可能会将问题归咎于父母的强硬态度,而非自身。
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往往会面临自我同一性与角色紊乱的矛盾,并由于自我意识的发展,逐渐开始寻求思维的独立性与批判性,进入质疑与辩论的活跃期,表现出对家长、教师“权威”的挑战(林崇德,李庆安,2005)。“引导-服从型”沟通模式既无法为初中生提供“尊重-对话型”的平等沟通环境,也缺乏“权威-服从型”的强力管控,反而更容易让初中生因为父母的“引导劝说”产生挫败感,进而在网络、手机等虚拟世界中寻求“被理解”和“被认可”。
(四)“孤独源自家庭”:学校联结对孤独中介作用的强化
本研究还揭示出学校联结在孤独与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存在贡献型调节效应。在未纳入学校联结的模型中,孤独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手机使用,这与先前研究一致,即手机可能作为寻求情感满足的方式,填补初中生在家庭沟通中情感支持的不足和交流的缺失。然而,引入学校联结及其与孤独感的交互项后,孤独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表明学校联结深刻影响着孤独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作用机制。深入分析发现,初中生学校联结水平调节了孤独在家庭沟通与问题性手机之间的中介效应,随着学校联结水平的提高,孤独的中介作用将被强化。
在高水平学校联结情境下,相较于“尊重-对话型”,“权威-服从型”与“引导-服从型”沟通均更易引发西部乡村初中生的孤独心理,进而加剧其问题性手机使用,即这两种沟通模式通过孤独正向预测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效应更为显著。这一结果与预期相悖:高水平学校联结非但没能减弱孤独对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负面影响,反而强化了这一过程。
可能原因是,家庭沟通所引发的孤独与学校联结产生的情感支持存在心理层面的实质差异,导致学校联结不仅无法缓解孤独,反而使初中生因社会比较加深了内生于家庭沟通的孤独。具体而言,在“权威-服从型”和“引导-服从型”沟通模式下,初中生因表达受限和选择缺失而感到情感压抑和自我怀疑,从而形成源于家庭情感支持缺失的深层孤独,即内在情感隔离;而学校提供的外部情感更多是社交支持,加之西部乡村教师数量普遍不足且师生流动频繁等因素,更使初中生难以在学校建立家庭般稳定的情感联结。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当个体在社会比较中意识到自身处于不利地位时,愤怒、不满等负面情绪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也由此出现(熊猛,叶一舵,2016)。因此,初中生在与同伴的比较中更能敏锐地意识到自身的情感脆弱性,学校联结反而加剧了孤独与压抑感,推动了问题性手机使用倾向。
为验证该推测,本文对学校联结与孤独进行回归,发现强学校联结的初中生孤独水平较弱(β = -0.204,t = -6.086,p < 0.001),进一步表明家庭和学校导致的孤独可能存在本质差异。这与 Weiss(1973)提出的互动主义孤独论一致,即孤独可分为情感孤独和社会孤独,前者源于离婚、丧偶、失去亲人等亲密关系缺乏所导致的情感联系缺失,对儿童而言则更侧重于亲子关系;而社会孤独则产生于社会交往匮乏,如与朋友接触频率低、活动往来少等。情感孤独更容易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社会孤独多导致焦虑、无聊与不安(王丽等,2017)。由此,本文认为,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的孤独主要源于不良家庭沟通引发的情感孤独,而非与学校联结相关的社会孤独,且情感孤独对问题性手机使用有更强烈的正向预测作用。
此外还应注意,“权威-服从型”沟通通过孤独预测问题性手机使用的中介效应弱于“引导-服从型”沟通。根据权威社会化理论,这可能是源于“权威-服从型”沟通中父母的显性控制更容易被初中生识别为外部压力,而不是自我认知错误。在这种沟通模式下所产生的“服从”效果,很可能只是麻木地“服从”,多表现为情感疏离的外在顺从,不会显著降低自我接纳程(Zuckerman,Marvin & Mary,1959),也不会对自身认知与判断能力产生怀疑。相比之下,“引导-服从型”沟通以温和方式实现服从期望,结合中国家庭中父母“牺牲”的传统特征,其体现为父母表面关注子女需求,但实际却“引导”子女应多“孝顺”父母,让子女“自愿”做出让步。在父母“引导”下的家庭资源配置方式会影响后代的认知和社会心理发展,易使青少年内化父母期望,并对自己的决策能力产生怀疑,从而陷入自我否定,而无法从学校联结中获得有效支持。即便在高水平学校联结下,初中生仍可能认为自己想法不够正确或难以融入群体。当学校联结无法有效缓解孤独时,网络提供的自由空间便使其更倾向于寻求虚拟支持,从而加剧其问题性手机使用倾向。因此,面对我国西部乡村近300万可能存在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的初中生群体,应对其“媒介过载”的关键在于建立基于深层尊重的亲子沟通,以弥补家庭内部的“链接失落”。
(五)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其一,横截面设计难以确定变量间因果关系,现实可能存在双向或更复杂的交互影响。其二,样本覆盖面受学校、年级、地理环境等因素限制。其三,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测量采用自我报告法,可能存在参与者的合理化偏差。其四,问卷设计未充分考察父母务工等关键因素,限制了对父母务工状态与亲子沟通关系的深入探讨。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是进一步扩大横纵样本覆盖面,追踪考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动态变化;二是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深入探究西部乡村家庭中父母务工等状态与亲子沟通的关系,获取手机使用习惯的质性数据,深化对现象的理解。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3期。
本期执编/曹书圆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mall.11185.cn/h5/#/bkGoodsDetails?spuId=113613&from=imgShare&dsId=zxSWChat&dsModule=c3df4964-af5d-40a8-d6cc-a768b5306e52 ,进入中国邮政微商城订阅本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进入官网下载原文
天臣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